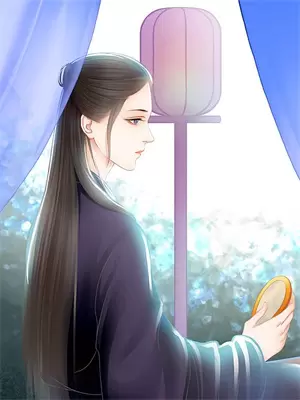我叫陈默,一个建筑师。我的人生,就像我画的图纸,每一条线都必须精准,
每一个角度都必须合理。我的妻子温晴,儿子小远,我们组成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,稳定,
和谐。直到小远的画,像一把没有刻度的角尺,将我所有的精准彻底打乱。
五岁的小远性格孤僻,不喜欢说话,唯一的爱好就是画画。他的画,曾经是我的骄傲。
他能用最简单的蜡笔,画出傍晚最复杂的晚霞。但从上个月开始,他的画风变了。所有的画,
无论主题是什么,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调,像老旧的默片。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,
是他的全家福。那是一张用A4纸画的画。画面中央,是我,温晴,还有被我们牵着的小远。
我们笑得很开心,头顶是明黄色的太阳。很正常的一幅画,除了一个细节。在温晴的身后,
紧紧贴着她的地方,多了一个人。一个全身涂满黑色的、火柴人一样的男人。他没有五官,
只是一个纯黑色的剪影,像一个烧焦的人形。最诡异的是,
太阳在我们的脚下投出了歪歪扭扭的影子,但那个黑衣男人的脚下,空空如也。他没有影子。
我第一次看到时,只是笑着用手指点了点那个黑影,问小远:“这是谁啊?
家里什么时候多了个新成员?”小远低着头,用力地抠着自己的手指,不说话。我没在意,
以为只是孩子的胡乱涂鸦。可第二天,第三天,小远画了更多的全家-福。
在公园里放风筝的我们,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们,在餐桌上吃饭的我们……每一张画里,
那个没有影子的黑衣男人,都如影随形。他永远站在温晴的身后,
像一个忠诚又诡异的守护者,用他那片纯黑的虚无,冷冷地盯着画外的我。
一种难以言喻的寒意,顺着我的脊椎一点点往上爬。我把所有画都收了起来,
锁进书房的抽屉里。我告诉自己,别胡思乱想,小孩子嘛,想象力丰富而已。
可那个没有影子的男人,已经在我心里投下了一片巨大的、无法驱散的阴影。
我开始控制不住地观察温晴。她还是那么温柔,每天准时做好晚饭,为我烫好第二天的衬衫,
睡前会给我一个晚安吻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。可我总觉得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她的笑容里,似乎藏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。她接电话时,会下意识地走到阳台。
她看我的眼神,偶尔会有一瞬间的闪躲。这些以前我从未在意的细节,如今像一根根针,
扎在我的心上。那个男人是谁?是真实存在的,还是只是我儿子幻想出来的?
如果他真的存在,他和温晴是什么关系?这个周末,我陪小远在他房间里搭积木。
我状似无意地,拿起一张新的全家-福,再次指着那个黑影,
用我能装出来的、最轻松的语气问:“小远,告诉爸爸,这个叔叔到底是谁啊?
”小远停下了手里的动作,他抬起头,
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混合着恐惧和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
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他说:“叔叔不让我告诉你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,
几乎能听到血液冲上头顶的声音。我强压着心头的狂跳,俯下身,
让自己看着更和蔼可-亲一些:“为什么不让告诉爸爸?”小远看着我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,
清晰地说道:“他说,他才是你的家人。”2“他说,他才是你的家人。”小远的这句话,
像一把生锈的钥匙,捅进我的脑子,然后狠狠地搅动了一下。一瞬间,我所有的理智和冷静,
都被搅成了一团黏腻的、散发着恶臭的浆糊。我呆在原地,全身的血都好像凉了。
我看着小远那双纯真的、甚至带着一丝困惑的眼睛,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,
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一个五岁的孩子,不会撒这样的谎。他的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小锤子,
敲在我濒临崩溃的神经上。叔叔。他叫他叔叔。这意味着,他见过这个男人。不止一次。
甚至,那个男人还对他说过话,教唆他,威胁他。而温晴呢?她知道吗?还是说,这一切,
根本就是她主导的?那个黑衣男人,是她的情人?他不仅想占有我的妻子,还想取代我,
成为我儿子的“家人”?这个念头一冒出来,就像一株疯狂生长的藤蔓,
瞬间缠住了我的心脏,勒得我喘不过气。我再也无法维持脸上的和善,我抓着小远的肩膀,
力气可能有点大,他疼得皱起了眉。“小远,看着爸爸。你是什么时候见到那个叔叔的?
在哪儿见的?他长什么样?”我的声音在发抖,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。
小远被我的样子吓到了,他瘪着嘴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“叔叔不让我说……他会生气……妈妈也会生气……”妈妈也会生气。我的心,
彻底沉入了谷底。那天下午,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
直到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味。我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,焦躁地踱来踱去。
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,用建筑师的逻辑去分析这一切。可能性一:小远在撒谎,
这只是他为了引起我们注意而编造的恶作剧。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,小远的性格,
不像会编造这么复杂谎言的孩子。可能性二:存在一个男人,他正在以某种方式,
接近我的儿子,甚至我的妻子。他是谁?他的目的是什么?
我强迫自己回忆最近几个月的生活。温晴是一家花店的老板,工作时间很自由。
她有没有什么异常?我想起了一个细节。大概从两个月前开始,温晴每天下午四点,
都会出门一趟。她说去见一个花材供应商。每次去,大概半个小时。以前我从未怀疑过。
但现在,这“消失的半小时”,成了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。我坐不住了。我冲出书房,
温晴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,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,给她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。
她哼着小曲,切着菜,岁月静好。可我看着她的背影,只觉得一阵阵发冷。
这个我爱了七年的女人,她的身体里,到底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?我走过去,
从背后抱住她。她的身体僵了一下,随即放松下来。“怎么了?今天这么黏人。”她笑着说,
侧过头想吻我。我躲开了。我闻着她头发上熟悉的洗发水香味,
用一种尽量平稳的声调问:“老婆,你下午见的那个供应商,谈得怎么样?
”她的动作停顿了一下,大概只有半秒钟,然后又恢复了自然。“还行吧,老样子。
一个很难缠的老头。”她撒谎了。我能感觉到。虽然她的语气天衣无-缝,
但那一瞬间的停顿,出卖了她。我的心,像是被人用手狠狠攥住。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
装作睡着了。温晴像往常一样,在我身边躺下,还帮我掖了掖被角。
我能闻到她身上沐浴后的清香,这曾是我最迷恋的味道,此刻却让我感到一阵恶心。
我睁着眼睛,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天花板,直到天亮。我决定了。我要查清楚。
不管那个男人是人是鬼,不管真相有多么不堪,我必须把它挖出来。这个家,
是我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,我不允许任何人,在我的图纸上,
画上一个来历不明的、没有影子的鬼东西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,
就会在心里长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森林。而我,已经迷失在这片森林里了。3接下来的几天,
我活得像个精神分裂的病人。在温晴和小远面前,我还是那个温和的丈夫,耐心的父亲。
我会笑着送她们出门,会在晚饭后陪小远玩游戏,会和温晴讨论周末去哪里郊游。我的演技,
连我自己都快信了。可一旦他们离开我的视线,另一张脸就会浮现出来。
一张充满猜忌、偏执、甚至带着一丝狰狞的脸。我成了一个潜伏在自己家里的间谍,
每一个角落,每一个细节,都成了我侦查的对象。我翻遍了温晴所有的东西。她的衣柜,
她的手提包,她的化妆品。我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,一根不属于我的头发,一张陌生的名片,
或者一缕不属于这个家的香水味。但我什么都没找到。温晴的生活,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
越是干净,我越是觉得不对劲。这就像一栋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建筑,完美到不真实,
那它的地基底下,一定埋着不可告人的东西。那“消失的半小时”,成了我唯一的突破口。
周一下午三点五十分,我提前从公司溜了出来,把车停在了一个能看到我们家小区的街角。
我像一个蹩脚的私家侦探,戴着一顶棒球帽,竖起衣领,感觉自己既可悲又可笑。四点整,
温晴准时从小区门口走了出来。她穿着一条素色的连衣裙,没有化妆,
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她没有开车,而是沿着人行道,慢慢地走着。我发动了汽车,
远远地吊在她身后。我的心跳得很快,手心全是汗。我既期待她走进某家咖啡馆或者酒店,
又害怕看到那一幕。那种感觉,就像等待法官宣判的囚犯。温-晴的路线很奇怪。
她没有走向商业区,反而走进了旁边一个老旧的居民区。那里的楼房都灰扑扑的,
墙上爬满了藤蔓,充满了年代感。她走进了一栋楼。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,跟了上去。
我看到她走上了二楼,在一个挂着“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站”牌子的门口停了下来,
然后推门走了进去。心理健康服务站?她来这里做什么?我不敢靠得太近,
只能在楼下的一个角落里等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半小时后,温晴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,甚至比进去前,还多了一丝放松。
我彻底懵了。这和我预想的任何一种可能都对不上。她不是去见情人,而是去看心理医生?
为什么?她有什么心理问题,是我不知道的?还是说,这只是一个幌子,
一个更巧妙的障眼法?我等到服务站快下班,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
里面只有一个看起来快退休的老医生,姓李。我谎称自己最近压力大,失眠严重,
想咨询一下。李医生很和善,给我倒了杯水,和我聊了起来。我旁敲侧击地,
提到了一个“穿着素色连衣裙,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女士”。李医生点了点头,说:“哦,
你说的是陈太太吧。她是个好妻子,也是个好妈妈,很坚强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
故作随意地问:“她……是有什么困扰吗?”李医生看了我一眼,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
他推了推老花镜,说:“陈先生,病人的隐私我不能透露。我只能说,
她承受了很多她本不该承受的压力。你作为丈夫,应该多关心她,多理解她。”这句话,
像一句意味深长的判词,让我更加云里雾里。回去的路上,我满脑子都是李医生的话。
温晴到底承受了什么压力?为什么她要瞒着我?难道,那个没有影子的男人,
和她的心理问题有关?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,而是温晴幻想出来的?
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一阵轻松,但很快,又被更大的恐惧所取代。如果我的妻子,
有我不知道的、严重的精神问题,那这个家,这个看似完美的等边三角形,是不是从一开始,
就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危楼?回到家,温-晴已经做好了晚饭。她看到我,
笑着说:“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?”我看着她温柔的笑脸,第一次,感觉到了彻骨的陌生。
我走过去,拥抱了她。我说:“老婆,辛苦了。”可我的心里,却在说:你到底是谁?
4和心理医生的谈话,并没有驱散我心头的迷雾,反而让这团雾变得更浓了。
温晴有心理问题。这个认知,比她有外遇更让我感到恐惧。因为后者,
我至少知道我的敌人是谁。而前者,我的敌人是虚无的,是看不见的,
它就藏在我妻子的身体里,藏在我们看似温馨的家里。我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猜下去了。
我需要证据,需要“看见”真相。一个疯狂的念头,在我心里滋生。我要在家里,
装上摄像头。这个想法让我感到羞愧和自我厌恶。家,是最后的港湾,
是卸下所有伪装的地方。而我,却要把这个地方,变成一个被监视的牢笼。我将从一个丈夫,
变成一个偷窥者,一个躲在暗处,窥探自己妻子和儿子一举一动的变态。
可是一想到小远画里那个没有影子的男人,一想到温晴那“消失的半小时”,
一想到心理医生那意味深长的眼神,我就觉得,我别无选择。我从网上,
买了一套最小的针孔摄像头。它们伪装成各种日常用品的样子,一个充电头,
一个烟雾报警器,甚至一个挂在墙上的装饰画。周末,我借口公司加班,
把温晴和小远送去了岳母家。然后,我一个人回到了这个空无一人的家里。房子里很安静,
静得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,在自己的家里,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我把摄像头,分别装在了客厅的吊灯上,小远房间的书架上,还有我们卧室的床头柜里。
每一个位置,我都精心计算过角度,确保能覆盖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又不容易被发现。
做完这一切,我坐在沙发上,看着这个我熟悉的家,感觉它变得无比陌生。墙壁,
不再是墙壁,而是隔绝秘密的屏障。家具,不再是家具,而是藏污纳垢的容器。
这个家里流动的空气,都变得粘稠而压抑。晚上,温晴和小远回来了。温晴还笑着问我,
加班累不累,给我放好了洗澡水。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,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有种强烈的冲动,
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,问她到底在隐瞒什么。但话到嘴边,又被我咽了下去。我害怕。
我害怕一旦撕开这层伪装,看到的,会是我无法承受的真相。从那天起,我的生活,
被劈成了两半。白天,我在公司,看似在工作,实际上,大部分时间,我都在用手机,
连接着家里的摄像头,像看一部实时直播的、无比沉闷的悬疑剧。画面里,温晴的生活,
一如既往的平静。她打扫卫生,侍弄阳台上的花草,陪小远画画。
小远还是会画那个黑衣男人,温晴看到了,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,什么也没说。一切,
都正常得可怕。我开始怀疑,是不是我自己疯了。是不是我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也许,
真的只是小孩子无聊的涂鸦,和妻子一点可以理解的私人空间。直到周三下午,四点整。
温晴像往常一样,对正在画画的小远说:“妈妈出去一下,很快回来。”然后,
她走进了卧室。我立刻将手机画面,切换到了卧室的摄像头。我看到温晴,从衣柜最深处,
拖出了一个上锁的旧皮箱。她熟练地打开锁,从里面,拿出了一样东西。
那是一部很老旧的、按键式的诺基亚手机。我的呼吸,瞬间停止了。
在这个人人用智能机的时代,她藏着这样一部手机,用来做什么?联系谁?
我看到她拿着手机,走到了窗边,似乎在编辑什么信息。她的表情,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。
几分钟后,她把手机,小心翼翼地放回皮箱,锁好,藏回衣柜深处。然后,她走出了家门。
我坐在办公室里,浑身冰冷。墙壁里的眼睛,终于看到了第一丝裂缝。而这丝裂缝背后,
藏着的,究竟是妖魔,还是鬼怪?55那部诺基亚旧手机,像一把刀,插在我心上。
它击碎了我最后的侥幸。一个正常的女人,不会在衣柜深处藏着这样一部功能机。
它只有一个用途——秘密联络。它就像地下工作者的电台,只在特定的时间,
向一个特定的、见不得光的接收者,发送加密的信号。我必须拿到那部手机。
机会很快就来了。周四晚上,温晴花店有活动,要很晚才回来。她提前做好了饭,
让我陪小远。她走后,我立刻冲进了卧室。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,像在打鼓。我拉开衣柜,
在最里面的角落,找到了那个旧皮箱。锁是普通的老式密码锁,三位数。
我试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,不对。试了她的生日,不对。试了我的生日,还是不对。
我额头上全是冷汗,心里越来越急。突然,我想到了小远。我试了小远的生日,
0-6-1-8。“咔哒”一声,锁开了。我的手颤抖着,打开了皮箱。里面,
只有那部黑色的诺基亚手机,安静地躺在一条旧的丝巾上。我拿起手机,冰冷的塑料外壳,
像一块寒铁。我按下了开机键。经典的开机音乐响起,在安静的房间里,显得格外刺耳。
我迅速翻看手机。通话记录是空的,收件箱是空的,只有发件箱里,有几十条已发送的短信。
所有的短信,内容都一模一样,都是空白的。没有文字,没有符号,就是一个纯粹的“空”。
而收件人,也永远是同一个号码,一个没有储存在通讯录里的、陌生的号码。发送的时间,
非常有规律,每天下午四点十五分。这太诡异了。每天发送一条空白短信,给一个空号?
这是什么暗号?还是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仪式?我试着拨打了那个号码。听筒里,
传来的不是彩铃,也不是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的提示音,
而是一段长长的、单调的“嘟——”声,像医院里心电图拉成直线的声音,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线索,在这里,以一种更诡异的方式,中断了。我把手机原样放回,锁好皮箱,恢复了一切。
然后,我瘫坐在地上,感觉自己的脑子快要烧坏了。这件事,已经超出了“婚外情”的范畴。
没有哪个情人,会用这种方式联络。这背后,一定藏着一个更深、更黑暗的秘密。
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,我听到了小远在房间里叫我。我赶紧收起情绪,走了过去。
小远正坐在他的小书桌前,又在画画。他看到我,举起手里的画,给我看。
又是一张全家-福。又是那个没有影子的黑衣男人。我的怒火和恐惧,再也压抑不住了。
我一把抢过那张画,撕了个粉碎。“不许再画了!以后不许再画这个东西!”我冲着他大吼。
小远被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发这么大的火。
我看着他满是泪水的小脸,心里一阵刺痛,后悔不已。我赶紧把他抱进怀里,不停地道歉。
“对不起,宝宝,
爸爸不是故意的……爸爸只是……只是有点害怕……”小远在我怀里抽泣着,过了好久,
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抬起头,用哭得红肿的眼睛看着我,小声说:“爸爸,
你不要怕他……”我愣住了。他继续说:“叔叔说,他不会伤害妈妈和你。
他只是……只是想回家。”想回家?他把这里当成家?我的大脑,被各种无法解释的线索,
搅成了一团乱麻。就在这时,我想到了那个社区心理医生,李医生。也许,他知道些什么。
也许,我应该换一种方式,去探寻真相。我决定,带小远,去见李医生。
6我预约了周六上午的时间。我对温晴说,小远最近性格越来越孤僻,
我想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,做个疏导。温晴的脸上,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,有惊讶,有担忧,
但似乎,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,如释重负。她没有反对,只是嘱咐我,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。
周六,我带着小远,再次来到了那个老旧的“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站”。李医生还是那么和蔼,
他给小远拿了些玩具和画笔,像一个邻家爷爷一样,和小远聊着天。小远在他面前,
似乎没有那么紧张。我坐在旁边,把小远最近画的那些“全家-福”照片,拿给李医生看。
我重点指出了那个没有影子的黑衣男人。李医生扶了扶老花镜,一张一张,看得非常仔细。
他的眉头,越皱越紧。他没有直接和我谈,而是转向小远,用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,
引导着他。“小远,能告诉李爷爷,画里的这个叔叔,是什么样子的吗?”小远看了我一眼,
我对他点了点头,鼓励他。他拿起一支黑色的蜡笔,在纸上,
又画出了那个熟悉的、没有影子的火柴人。“他很高,很瘦。”小远一边画,一边小声说,
“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。我看不到他的脸,他的脸……是黑的。”“那,
为什么他没有影子呢?”李医生继续问。小远停下了笔,他想了很久,
似乎在努力回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。然后,他抬起头,看着我们,
用一种无比认真的语气说:“因为,叔叔总是站在灯下面。但是,灯照不到他。
”灯照不到他。这句话,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。我一直以来的调查方向,
都是错的。我执着于寻找一个真实存在的人,一个温晴的情人,一个潜在的罪犯。
可小远的描述,根本不是在描述一个“人”。影子,是光被物体遮挡后形成的。
一个人站在灯下,怎么会没有影子?除非……除非他本身,
就是一道不被光所容纳的“影子”。我的调查方向,第一次,从现实的“婚外情”,
不可控制地,滑向了“非自然”的领域。我感觉后背的冷汗,刷地一下就冒出来了。
李医生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让助手带着小远去隔壁房间玩,然后,
表情严肃地看向我。“陈先生,这件事,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”他说,
“孩子是不会撒谎的,尤其是在这种潜意识的绘画里。他画出来的,就是他‘看到’的。
”“他看到了什么?鬼吗?”我几乎是脱口而出。说出这个字的时候,我自己都觉得荒谬。
我是一个建筑师,一个相信数据和逻辑的唯物主义者。李医生摇了摇头。“我不相信鬼神。
但在心理学上,有一种解释。这个‘没有影子的男人’,可能不是一个外部的存在,
而是一个……内部的投射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我完全听不懂。“意思是,他可能,是你,
或者你妻子,内心深处,某个被压抑、被遗忘的创伤记忆的具象化。孩子是最敏感的,
他们能感受到成年人世界里,那些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暗流。小远,
可能‘看’到了你们家庭里,那个看不见的‘伤口’。”伤口?我们家有什么伤口?
我努力地回忆着,我和温晴从恋爱到结婚,一直很顺利。我们的家庭,
就像我设计的那栋得奖的建筑,结构稳定,功能完善,没有任何瑕疵。“陈先生,
”李医生看着我,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,“你确定,你的记忆,是完整的吗?”他的话,
像一把锥子,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。记忆?我的记忆,难道会有问题吗?7李医生的话,
像一颗定时炸弹,埋在了我的心里。“你确定,你的记忆,是完整的吗?”这个问题,
在我脑子里,反复回响。我开始疯狂地回忆我的过去。我记得我大学毕业,记得我进设计院,
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温晴,记得我们结婚,记得小远出生……一切都清晰得像是昨天才发生。
我的记忆,没有任何断层。李医生一定是搞错了。可是,那个没有影子的男人,那部旧手机,
温晴的反常……这一切,又该怎么解释?我陷入了更深的混乱。我开始失眠,
整夜整夜地做噩梦。梦里,全是小远画的那些画,那个黑衣男人,从画里走了出来,
无声地站在我的床边,冷冷地看着我。我的精神状态,越来越差。我变得易怒,多疑,
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草木皆兵。温晴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,她对我愈发的小心翼翼,
甚至有些讨好。但她越是这样,我越是觉得她心里有鬼。我们之间的气氛,降到了冰点。
曾经温馨的家,如今安静得可怕,我和温晴,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。
我们就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,彼此防备,彼此猜忌。终于,
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来了。周二晚上,我提前回了家。我看到温晴,
又拿着那部诺基IA手机,站在阳台上。她似乎在打电话,而不是发短信。她的背影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