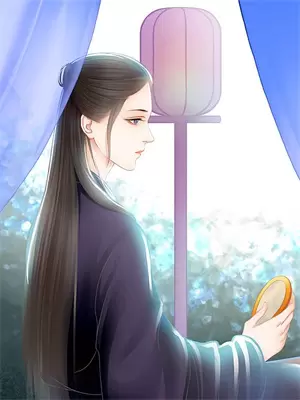第七天了。雨还在下,黏腻又固执地敲打着窗玻璃,把世界染成一片灰蒙蒙的氤氲。
城市依旧喧嚣,车流碾过湿漉漉的马路,发出永无止息的嘶响,可这间屋子,却安静得可怕。
钟摆的每一次滴答,都像钝刀割在心上。周屿的气息,正被这种寂静一点一点吞噬。
他常坐的那张皮质扶手椅,凹陷的轮廓还在,却没了体温。
他随手搁在茶几上的那本《漫长的告别》,书签还夹在第三章。
一切都维持着他七天前那个清晨离开时的模样,除了他本人,像一滴水蒸发了。
警方已经备案,调查不温不火。所有人都暗示我,一个成年男性,或许只是需要“静一静”。
可我知道,不是。周屿不是这样的人。他连出差都会在行李箱夹层里给我留张小纸条,
怎么会忍心让我陷入这种无边无际的猜测和恐慌?绝望像藤蔓一样勒紧我的喉咙。
我几乎要相信那些善意的劝慰了,也许他真的只是……厌倦了?直到今天下午,收拾书房时,
指尖无意间划过书架侧板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凸起。鬼使神差地一按,
旁边一本厚重的《建筑设计规范》后面,弹出一个扁平的暗格。里面没有珠宝,
没有机密文件,只有一本深蓝色布面、没有任何标识的笔记本。心脏猛地一缩。
我认得这个本子,是去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,封皮是他喜欢的、像深海一样的颜色。
他当时笑得眼睛弯弯,说要用它来记录最重要的东西。后来我问起,他只说还没想好写什么。
原来,他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指尖带着微颤,翻开了第一页。那熟悉、挺拔的字迹,
像一颗子弹,瞬间击穿了我所有的伪裝。“薇薇,如果你看到这本日记,
说明我的计划成功了。别怕,跟着我留下的路标往前走。”我的呼吸停滞了。计划?
什么计划?成功的标准……就是他消失不见吗?巨大的荒谬感和寒意沿着脊椎攀升。
我强迫自己一页页往下读。日期是从三个月前开始的。起初的内容像寻常的工作记录,
夹杂着一些零散的思绪。但很快,我发现了规律。
他用一种只有我能完全理解的、近乎密码的方式,
记录着一些“发现”——关于他供职的建筑设计公司,关于某个市政翻修项目,
关于一笔笔去向暧昧的资金流动。他写得隐晦,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冷峻,让我胆战心惊。
他不是在记日记,他是在整理罪证。而他怀疑的对象,直指公司那位权势煊赫的董事长,
陈向明。日记的页脚,时常有他随手画下的结构草图,或是复杂的力学公式。
他像是在推演什么,评估着某种风险。我的心跳随着那些越来越密集的数字和图形不断加速。
然后,我翻到了一页,里面夹着什么东西。拈起来,是一张微微泛黄的纸片。
是两张连在一起的、去年夏天那部我们一起看了三遍的文艺电影票根。我记得那天,
空调开得太足,我冻得直往他怀里钻,他笑着用外套裹住我,荧幕上的光映在他眼里,
像落满了星星。散场后,我们在午夜空旷的街上走了很久,讨论着那个开放式的结局,
他说:“薇薇,有些真相,或许不知道反而更幸福。”当时只道是寻常。此刻,
这张承载着温暖记忆的票根,却像一块冰,烙在我的指尖。他为什么把它夹在这里?是提醒,
是慰藉,还是……诀别?越往后翻,这样的“纪念品”越多:一片干枯的银杏叶,
来自我们初吻的公园长椅旁;一张登机牌的残角,
脾气撕碎又被他小心翼翼粘好的、画着一只气鼓鼓小猫的便签纸……他把我们相爱过的证据,
一点点镶嵌进这条通往未知黑暗的路上。每一件小东西,都像一记温柔的耳光,
打在我已然麻木的脸上。泪水模糊了视线,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,抹去水渍,
才能看清接下来的文字。他在引导我。用他留下的专业图表,
暗示着那些违规操作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;用他标记出的几个关键日期和地点,
串联起可能的证据链。他甚至在某一页,
详细描述了一种特定型号的建筑胶粘剂在受潮后性能衰减的数据,
旁边用红笔重重圈出:“关键物证,送检机构应为……”我像个被操控的提线木偶,
跟着他预设的剧本,一步步走向那个他早已窥见的深渊。我利用我作为刑警的专业知识,
循着他留下的蛛丝马迹,开始暗中调查。过程比想象中更惊心动魄,
几次险些被陈向明的人察觉。但每次犹豫退缩时,看到日记本里那些温暖的“纪念品”,
就好像听到周屿在我耳边说:“别怕,薇薇,你可以的。”真相如同一个巨大而丑陋的怪物,
渐渐浮出水面。陈向明为了巨额利益,在多个项目中使用劣质材料,勾结监管,草菅人命。
而周屿,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,触及了核心秘密。他意识到自己被监视,危险近在咫尺。
他没有选择报警,因为他不确定警局内部是否有陈向明的保护伞。
他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——用自己的“备失踪”,来引爆一切。而他选择了我,
他最亲密的爱人,作为他最后的复仇使者。日记接近尾声。我的手指因为长时间紧握而僵硬,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,每一次跳动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。终于,我翻到了最后一页。
页面上只有一行字,墨迹深重,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:“现在,亲手逮捕杀死我的真凶吧,
亲爱的侦探小姐。”时间,在那一刻凝固了。窗外城市的噪音骤然消退,
世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和擂鼓般的心跳。杀死他的……真凶?这几个字像淬了毒的针,
狠狠扎进我的脑海。陈向明?是的,陈向明是元凶,是他逼死了周屿!
可是……“亲手逮捕”……一个冰冷彻骨的念头,毫无征兆地炸开。我猛地抬起头。
书桌正对着的,是镶嵌在墙里的一面穿衣镜。平日里用它整理仪容,此刻,
它却像一道通往地狱的入口。镜子里,清晰地映出我的身影。穿着笔挺的警服,
肩章上的银色徽记在灯光下闪着冷光。因为连日的奔波和悲伤,脸色苍白,眼圈乌青,
但那双眼睛……那双眼睛里,除了无尽的悲恸,还有什么?是了。周屿留下的所有线索,
都指向一个内部泄密的可能性。
他那些关于送检机构、关于避开常规流程的提醒……他怀疑警局有内鬼。
而他最后这句话……“杀死我的真凶……”不是我泄露了那次秘密调查的行动时间吗?
虽然是无心,
在争吵后向“信任”的伴侣抱怨了几句工作的不顺……是陈向明巧妙安插在我身边的棋子吗?
那个对我体贴入微的“恋人”?不。镜子里那双写满痛苦和恐惧的眼睛,
告诉了我另一个答案。一个我从未敢触碰的答案。周屿的计划,
不仅仅是让我揭露陈向明的罪行。他的计划,是让我看清我自己。
日记本从我颤抖的指尖滑落,掉在地毯上,发出沉闷的一声。我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,
抬起另一只手。动作僵硬得像一个生锈的机器人。手指伸向腰侧,触碰到那冰冷坚硬的金属。
一副手铐。银色的镣铐,在室内光线下,泛着和我脸色一样苍白的光。我一步一步,
走向那面镜子。镜子里,那个身穿警服的女人,也正一步一步,向我走来。她的眼神,
从最初的混乱、难以置信,渐渐变成一种死寂的、深渊般的绝望。我们的影子,
在镜面中一点点重合。我抬起颤抖的、戴着白手套的手。“咔嚓。”一声轻响,
在死寂的书房里,清晰得刺耳。冰凉的金属,圈住了我同样冰凉的手腕。镜子里,
那个身穿警服的女警,手腕上,也多了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。泪水,终于决堤而出,
汹涌地模糊了镜中那张痛苦扭曲的脸。周屿,这就是你为我铺好的,最后的路吗?
让我成为侦探。也让我,成为囚徒冰冷的触感从手腕蔓延至全身,
镜中的影像与现实的界限在泪水中模糊。我是侦探,也是囚徒。周屿,你用最残忍的方式,
给了我答案,也给了我审判。就在这绝望的顶点,几乎要被负罪感吞噬的那一刻,书桌上,
那个看似已经终结的日记本,突然发出了极其轻微的、电子设备启动时的“嘀”声。我一怔,
泪水凝固在脸颊。目光机械地转向声音来源。深蓝色的日记本封皮一侧,
一个我从未留意过的、细如发丝的缝隙里,透出了微弱的蓝光。紧接着,
书本内置的微型扬声器里,传出了一个声音——那个我思念入骨、以为永诀的声音,
带着一丝疲惫,却异常清晰。“薇薇,如果听到这个,说明你最坏的可能……没有发生。
”是周屿!他还活着?巨大的冲击让我几乎站立不稳,猛地扶住书桌。
手腕上的手铐与木质桌面碰撞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“对不起,用这种方式测试你。
”他的声音继续平静地流淌,像在叙述一个早已编排好的剧本,“日记是真的,
陈向明的罪证也是真的。我的‘失踪’,是为了引蛇出洞,也是为了……保护你,
并确认一件事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里带上了一种复杂的情绪,混合着释然与更深沉的痛楚。
“我怀疑警局有内鬼,很久了。泄露的消息精准得可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