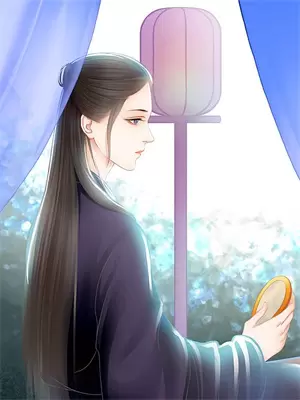别回头我在法医档案室发现一张1998年的尸体照片,死者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
调查时总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:“别回家。”今晚推开门,
着和照片里相同的红绳圈——而背后传来我妈温柔的声音:“当年死的双胞胎……其实是你。
”档案室惊魂档案室的灯,接触不良,一下,一下,闪着。惨白的光跌在覆满灰尘的纸箱上,
空气里全是旧纸张和某种类似福尔马林,但又更陈腐的气味。我捂着鼻子,
在“98年未归档杂项”的箱子里胡乱翻着。指尖触到一个硬质相纸的边角,抽出来。
是张黑白照片,有些受潮,边缘晕开黄褐的水渍。照片上是一具女尸,半埋在泥里,
脸正好对着镜头。长发黏在额颊,五官清晰。我浑身的血,霎时冻住。那眉眼,那鼻梁,
那因为死亡微微张开、似乎还想说什么的嘴唇……每一寸,都和我,一模一样。
胃里一阵翻搅,强忍着才没吐出来。心脏擂鼓一样撞着胸腔。这不可能……1998年?
我明明是98年生的。一股没来由的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。我猛地回头。档案室深处,
货架投下大片、大片沉重的阴影,寂静无声。只有头顶那盏破灯,还在固执地,
吱呀——明灭。把照片塞进外套内袋,几乎是逃离了那里。接下来的半天,
耳边总萦绕着什么,细碎,模糊,像电流的杂音,又像隔着墙壁的絮语。集中精神去听,
又没了。直到下班,挤进地铁拥挤的人潮,那声音陡然清晰起来,贴得极近,
一股凉气钻进耳廓:“别……回家。”我一个激灵,四周张望。一张张疲惫又陌生的脸,
各自对着手机,没人看我。冷汗湿透了内衬。别回家?为什么?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。
越靠近家门,心跳得越厉害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,跺脚也不亮。黑暗像有实质,
沉甸甸地压过来。钥匙插进锁孔,转动。咔哒。门开了。客厅没开灯,
只有厨房方向透来一点微弱的光。我吸了口气,换鞋,走向厨房。目光落在不锈钢的灶台上。
那里,空空荡荡,只摆着一件东西。一根褪色、发暗的红绳圈。编织的手法很旧,
绳结的方式……和照片里,死者手腕上套着的那根,一模一样。血液呼啸着冲上头顶,
又瞬间褪去,留下彻骨的冰凉。照片在我口袋里,像个烧红的烙铁。就在这时。
一个无比熟悉,甚至称得上温柔的声音,从我身后,紧贴着我的后背,响了起来。
是我妈的声音。“照片看到了?”“当年死的那个双胞胎……”她顿了顿,
气息拂过我的后颈。“其实是你啊。”好的,我们继续这个故事。
2 红绳之谜那声音像一把冰锥,凿穿了我最后的理智。是我妈的声音,每一个语调,
每一个尾音,都分毫不差。可这内容……这内容……“当年死的双胞胎……其实是你啊。
”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重量,砸在我的耳膜上,然后沉入四肢百骸,
冻僵了所有的动作和思维。照片里的“我”躺在泥泞中。灶台上那根诡异的红绳。现在,
是母亲宣判了我的“死亡”。我猛地转过身,颈椎甚至发出了“嘎达”的轻响。身后,
空无一人。只有客厅通往卧室的走廊入口,那片更深沉的黑暗,静默地张着嘴。刚才那声音,
分明就是贴在我背后说的!“妈……?”我的声音干涩发颤,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微弱不堪。
没有回应。死寂。比刚才在档案室感受到的,更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连窗外偶尔路过的车声都消失了,世界仿佛被抽成了真空。
我的目光死死锁住灶台上那根红绳。它像一条凝固的血痕,又像一道邪恶的符咒。
照片中的女尸手腕上,就是它。现在,它出现在我家,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。
“别回家……”那个警告,此刻像淬了毒的针,反复扎刺着我的神经。它不是阻止我回家,
它是提醒我,这里,可能根本不是我的家!我颤抖着手,再次摸出那张照片。
借着厨房微弱的光,死死盯着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之前只觉得惊悚,现在,
却生出一种荒谬的熟悉感,仿佛在凝视一面扭曲的镜子,或者……一段被埋葬的过去。
心脏狂跳,几乎要挣脱胸腔。我强迫自己移动僵硬的腿,一步一步,挪向父母的卧室。
他们的房间门虚掩着,里面黑漆漆的。“妈?爸?”我提高声音,试图驱散那摄人的恐惧。
依旧没有回应。我鼓起勇气,推开房门。手指摸到墙上的开关,“啪”一声,灯亮了。
房间里整洁得过分。床铺平整,桌面干净,甚至带着一种无人居住的清冷。
我快步走到床头柜前,拉开抽屉——里面是些杂物,药瓶、老花镜、几本旧书。没有异常。
我又冲到衣柜前,猛地拉开。里面挂着父母常穿的衣服,但……好像少了些什么?
我说不上来,只是一种强烈的直觉,这里的气息不对。
难道……一个可怕的念头窜入脑海:他们不在家?那刚才的声音……我冲出父母卧室,
几乎是扑到玄关的座机电话前,手指哆嗦着按下母亲的手机号码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听筒里传来的等待音,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快接啊!快接电话!
告诉我这只是个噩梦!告诉我你就在楼下遛弯!“喂?”电话通了!
那边传来母亲如常的声音,背景音有些嘈杂,像是在街上。“妈!”我几乎是喊出来的,
“你在哪儿?!”“我在你张阿姨家打麻将呢,怎么了?听着声音不对啊。
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关切,还有麻将牌碰撞的哗啦声。打麻将?在张阿姨家?
那……刚才家里那个声音……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,我握着话筒的手指冰冷彻骨。
“你……你一直在家吗?刚才……有没有回来过?”我语无伦次。“没有啊,
吃了午饭就过来了,这刚开第二圈。出什么事了?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
”母亲的声音真的着急起来。“……没,没事。”我喉咙发紧,“可能……可能听错了。
你……你玩吧。”我几乎是摔下了电话,浑身脱力地靠在墙上,冷汗已经浸透了后背。
母亲不在家。那刚才在我背后说话的是谁?那个模仿得惟妙惟肖的……东西?
“别回家……”它不是在阻止我回到这个物理的空间,它是警告我,
不要回到这个被“它”侵入了的“家”!我的目光再次投向厨房灶台,
那根红绳静静地躺在那里,像一个嘲讽的句点。不,不能待在这里!我必须离开!立刻!
马上!我冲向门口,手刚触到门把手——“咔哒。”一声轻响,来自我身后父母卧室的方向。
我全身的汗毛瞬间倒竖!极缓慢地,一点点回过头。父母卧室的灯,不知何时,灭了。
而那扇我刚才打开的房门,此刻,正无声地、缓缓地,从里面被关上了一条缝。缝隙后面,
是无边的黑暗。以及,黑暗中,似乎有一道视线,正牢牢地锁定了我。门缝后的黑暗,
浓稠得像是实体。那道视线黏在我的背上,冰冷,带着非人的审视。
我甚至能感觉到它滑过我的颈椎,一寸一寸,如同湿滑的鳞片。跑!
这个念头像电流一样击穿了我的僵直。我猛地拧动门把手——纹丝不动!锁舌卡得死死的,
像是焊在了一体。我发疯似的摇晃、撞击,单薄的木门发出沉闷的响声,却固若金汤。
我被困住了。和那个“东西”,一起困在了这个曾经称之为“家”的囚笼里。
背后的视线没有移动,但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从卧室门缝里弥漫出来,空气变得粘滞,
呼吸开始困难。不能坐以待毙!我猛地转身,背靠着冰冷的大门,
眼睛死死盯住那扇虚掩的卧室门。厨房……对,厨房有刀!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过去,
撞在冰冷的灶台上,一把抓起了最沉的那把剁骨刀。金属的冰凉触感稍微拉回了一丝理智,
但恐惧依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心脏。“谁……谁在那里?!”我朝着卧室方向嘶吼,
声音破裂,带着自己都陌生的哭腔。没有回应。只有死寂,以及死寂中那无声的凝视。
握着刀柄的手心里全是冷汗。我慢慢移动,背部紧贴着墙壁,试图绕到客厅另一侧,
获取更好的视野,或者找到其他出路——阳台,或者窗户!就在我移动到客厅中央,
视线短暂脱离卧室门缝的刹那——“嘻嘻……”一声极轻、极快的笑声,像冰冷的针,
猝不及防地刺入我的耳膜。是女人的笑声。年轻,甚至带着点娇俏,但毫无温度,
只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恶意。不是母亲的声音!我霍然转头,目光再次聚焦于那扇门。缝隙,
好像……宽了一点点。里面的黑暗似乎流动了一下,有什么东西,极快地缩了回去。
冷汗顺着我的鬓角滑落。那不是母亲,绝对不是!它刚才只是在模仿!现在,它似乎懒得,
或者说不屑于再伪装了。双胞胎……死的那个是我?如果死的是我,那现在站在这里,
拿着刀,浑身发抖的……是谁?如果死的是我,那当年下葬的是谁?父母知道吗?
他们为什么隐瞒?无数个问题像沸腾的气泡在我脑海里炸开,几乎要将我的头骨撑裂。
灶台上的红绳,此刻在我眼角的余光里,像一只窥伺的眼睛。我死死盯着卧室门,
脚步极其缓慢地向阳台方向挪动。阳台窗户或许可以打破,下面是二楼,
跳下去或许……“嗒。”一声轻响,从我刚离开的父母卧室方向传来。不是关门声,
更像是……指甲轻轻敲击木头的声音。我的动作瞬间定格,心脏停跳了一拍。
“嗒……嗒……”敲击声很有节奏,不紧不慢,带着一种戏谑的意味,
仿佛在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它不是在门板上,那声音……更像是在……我猛地意识到,
那声音传来的方向,是父母的床!是实木的床头发出的声音!它已经不在门后了?
它什么时候……恐惧像冰水一样兜头浇下。我看不见它!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!
“嘻嘻……”那冰冷的笑声再次响起,这一次,近在咫尺!仿佛就在我的耳边!
我甚至能感觉到那股带着腐朽气息的凉风,吹动了我的发丝!“啊——!
”我失控地尖叫起来,手中的剁骨刀胡乱地向身后挥舞,砍中了空气,带起一阵徒劳的风声。
什么都没有。身后空空如也。但那股被窥视、被贴近的感觉,丝毫没有减弱。
我崩溃地冲向阳台,手刚碰到阳台门的拉手——“叮铃铃——!”客厅的座机电话,
毫无征兆地,炸响起来!尖锐的铃声像一把锯子,切割着紧绷的神经。我吓得几乎跳起来,
猛地回头。电话机在玄关的矮柜上,屏幕亮着,显示着一个熟悉的号码——是母亲的手机号。
她不是还在张阿姨家打麻将吗?她为什么又打来?接?还是不接?刚才通话时,
她那边的背景音……真的是麻将声吗?现在回想起来,那哗啦声,是不是……太单调,
太规律了点?铃声固执地响着,一声接一声,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刺耳,
仿佛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催促。而我背后,阳台玻璃门外,映出的不再是熟悉的街道夜景。
玻璃上,不知何时,蒙上了一层浓重的、化不开的白雾。仿佛有什么东西,刚刚在那里,
对着里面,呼出了一口冰冷的寒气。我僵在原地,前有催命的电话铃声,
后有未知的白雾和那个无处不在的“它”。手里的刀,沉重得几乎要脱手落下。那个声音,
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扭曲的笑意,再次贴着我耳畔响起,
这次清晰无比:“接电话呀……”“听听‘妈妈’……还想告诉你什么。”好的,
我们让这个故事走向更深的迷雾。
3 双生之咒“接电话呀……”“听听‘妈妈’……还想告诉你什么。
”那耳语带着粘稠的恶意,钻进我的脑子。我握着刀的手抖得厉害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
试图用疼痛维持最后一丝清醒。电话铃还在疯狂嘶鸣,屏幕上“妈妈”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。
阳台玻璃上的白雾开始凝结成水珠,一道道滑落,像无声的泪。跑!必须离开这个房间!
我放弃阳台,猛地转身,目光扫过客厅——卫生间!那里有窗户,虽然小,但或许能钻出去!
我跌跌撞撞冲过去,一把拉开卫生间的门。“啪嗒。”有什么东西掉在了脚边。我低头。
是一根红绳。和灶台上那根一模一样,褪色,发暗,编织手法古老。
它刚才……是挂在门把手内侧的吗?心脏骤停了一瞬。我没时间细想,一脚踢开红绳,
反手锁上卫生间的门,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息。狭小的空间给了我一点点虚假的安全感。
窗户外是楼下的绿化带,不高。我扑过去,用力拧窗栓——锈死了!纹丝不动!
我举起剁骨刀,用刀柄狠狠砸向玻璃!“砰!砰!砰!”沉闷的响声在狭小空间里回荡,
玻璃却异常坚固,只留下几个白点。就在这时,外面的电话铃声,戛然而止。
绝对的寂静猛地降临,比之前的噪音更让人心悸。我停下动作,屏住呼吸,耳朵紧贴着门板,
倾听外面的动静。什么都没有。它走了吗?不……一种细微的、湿漉漉的摩擦声,
在门外响起。“嘶啦……嘶啦……”像是什么东西拖着沾满粘液的躯体,
在地板上缓慢地移动。声音越来越近,停在了卫生间门外。我死死捂住嘴,
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浑身肌肉绷紧得像石头。门把手,轻轻转动了一下。“咔哒。
”锁扣发挥着作用。门外的“东西”似乎停顿了。几秒钟的死寂。然后,
一种低低的、断断续续的哼唱声,从门缝底下钻了进来。调子很古怪,不成曲调,
带着某种遥远的、童谣般的韵律,却又扭曲变形,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哼唱声停住了。接着,
那个模仿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,这一次,它就紧贴着门板,几乎与我面对面:“开门啊,
孩子……”“让妈妈看看你……”它的声音依旧温柔,却带着一种冰冷的、非人的质感,
像毒蛇的信子舔舐着耳膜。我握紧刀,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“你不是我妈!
”我用尽力气低吼。门外沉默了一下。然后,它笑了。不是之前的“嘻嘻”,
而是一种低沉、沙哑,仿佛来自喉咙深处的,破碎的笑声。
“呵呵……是啊……”“那你猜猜……”“你‘妈妈’现在……在哪里呢?
”这句话像一把冰锥,狠狠凿穿了我最后的心理防线。张阿姨家?那通电话?
如果门外这个不是,那给我打电话的……真的是我妈吗?还是……另一个?
混乱和恐惧像沼泽一样淹没了我。我猛地想起档案室的那张照片,
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……红绳……记忆的碎片疯狂旋转,试图拼凑出一个恐怖的图景。
双胞胎……一个死了……一个活着……红绳是标识?是谁的标识?死的是谁?
活下来的……又是谁?门外的“东西”似乎失去了耐心。“砰!
”一声沉重的撞击砸在门板上,整个卫生间都在震动!“砰!砰!”它开始疯狂地撞门!
木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,锁扣螺丝在一点点松动!我绝望地举起刀,对准门口。
完了…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——“咚!咚!咚!”客厅方向,传来了清晰、有力的敲门声!
还有一个男人粗犷的喊声:“里面怎么回事?!吵什么吵!再闹报警了!”是邻居!
是被我砸玻璃和撞门声引来的邻居!门外的撞击声,瞬间停止了。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,
如潮水般退去。哼唱声,低语声,全部消失了。一切重归寂静,
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。只有地板上那根刺眼的红绳,和被撞得微微变形的门板,
证明着那不是梦。我瘫软在地,眼泪和冷汗混在一起,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席卷全身。
邻居还在外面敲门询问。我得救了吗?那个“东西”……走了?我颤抖着,慢慢爬起身,
手伸向门锁……要不要开门?我的目光,再次落在地上那根红绳上。它静静地躺在那里,
像一个冰冷的问号,又像一个未完的……句点。我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,
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,只剩下胸腔剧烈的起伏和劫后余生的颤抖。门外,
邻居粗声粗气的询问和逐渐远去的脚步声,成了现实世界唯一的锚点。它走了。
那个东西……暂时离开了。得救了?不,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自己掐灭。灶台上的红绳,
门缝后的黑暗,还有那贴着耳朵的冰冷低语……这一切都像毒液,
已经注入这间房子的每一寸墙壁。我只是获得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。
地上那根从卫生间门把手掉落的红绳,刺眼地躺在那里。我死死盯着它,
恐惧慢慢被一种扭曲的好奇和求生的狠厉取代。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,我必须知道真相。
那个“东西”问我妈妈在哪里……张阿姨家?那通电话……我手脚并用地爬过去,
捡起那根红绳。触手是一种异常的阴冷,仿佛能吸走指尖的温度。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,
冰冷的触感反而让我混乱的大脑清醒了一点。扶着洗手台艰难站起,
镜子里映出一张惨白、惊恐、被汗水和泪水弄得一塌糊涂的脸。这是我的脸吗?
还是照片里那个死人的脸?深吸一口气,我猛地拉开卫生间的门。客厅里空荡荡的。灶台上,
之前那根红绳不见了。仿佛刚才的一切真的只是我的幻觉。
但空气中残留的那丝若有若无的、混合着土腥和腐朽的冰冷气息,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。
我快步走到座机电话旁,屏幕上还显示着母亲的未接来电。我回拨过去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等待音再次响起,这一次,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。快接,
快接啊妈妈!告诉我你安全!“喂?”母亲的声音传来,背景依旧是哗啦啦的麻将声,
听起来比刚才更嘈杂一些,似乎换了一桌,或者有人在大声说笑。“妈!”我急切的打断她,
“你还在张阿姨家吗?你没事吧?”“在啊,我能有什么事?刚打完一圈。你怎么了?
声音怎么成这样了?听着不对劲啊!”母亲的声音带着真切的担忧。“我……我没事。
”我强迫自己冷静,大脑飞速运转,“妈,你……你记得我小时候,有没有什么……比如,
红绳编的手环之类的东西?”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只有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持续着。
这沉默像一只无形的手,扼住了我的喉咙。“红绳?”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,
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,或者说……警惕?“你怎么突然问这个?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,
谁还记得清。”她在回避!“妈!你好好想想!这很重要!非常非常重要!
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“……好像……是有过吧。”母亲的声音压低了些,
背景的麻将声也似乎远了点,她可能走到了安静的地方,“你和你……那时候,
好像是有过一对。后来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你问这个干嘛?”你和你……她顿住了那个词。
是“你和你妹妹”?还是“你和你姐姐”?照片上的双胞胎……红绳……“那对红绳,
是什么样的?有什么特别吗?”我追问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“就是普通的红绳编的,
小孩子戴的玩意儿,能有什么特别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急于结束话题的烦躁,
“行了行了,我这儿还打着牌呢,没事我挂了啊,你早点休息,别胡思乱想!”“妈!别挂!
你听我说……”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”忙音响起,她挂断了。她挂断了!在我如此急切,
近乎崩溃的时候,她竟然就这么挂断了电话!那种敷衍,那种急于摆脱的态度,
根本不像是面对女儿可能遭遇危险时的正常反应!冷汗再次浸透了我的后背。不对劲。
一切都不对劲。母亲的态度。那根消失又出现的红绳。那个能完美模仿她声音的“东西”。
还有它最后那句——“你‘妈妈’现在……在哪里呢?”一个可怕的念头,
像毒蛇一样钻入我的脑海:电话那头的,真的是我妈妈吗?那背景音里的麻将声,
会不会……也只是另一种更高明的模仿?如果连最亲的人都不能信任……我猛地转身,
目光扫视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。这里不再安全,这里充满了谎言和未知的危险。
我必须找到答案,否则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夜晚。
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父母卧室那扇紧闭的房门上。刚才,那个“东西”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
那里,会不会藏着什么?恐惧依旧存在,但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支撑着我。
我握紧了手里的剁骨刀和那根冰冷的红绳,一步步走向那扇门。手放在门把手上,冰凉。
我深吸一口气,猛地推开!房间里和我之前检查时一样,整洁,冷清。但这一次,
我注意到了不同。床底。父母那张实木大床的床底,靠近我这边床头柜的位置,
隐约露出了一小角不同于深色地板的颜色。像是……纸?或者布料?我蹲下身,
用刀尖小心翼翼地去够。碰到了。是硬质的卡纸。我慢慢把它拨了出来。是一张照片。
一张彩色照片,比档案室那张清晰得多。照片上,是一对穿着同样小花裙的双胞胎女孩,
看上去大约三四岁,笑得天真烂漫。她们的手腕上,各自戴着一根鲜红的绳圈。
而抱着她们的女人,是年轻时的母亲,她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。
我的目光死死锁在其中一个女孩的脸上。那眉眼,那笑容……是我。绝对是我。那么,
另一个……我的呼吸停滞了。照片里另一个女孩,她的脸……她的脸,
分明就是档案室照片里那个死去女孩的脸!也是……我刚才在卫生间镜子里看到的脸!
她就是那个“死者”!可如果她是死者,那我是什么?照片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,背面朝上。
那里,用娟秀又带着一丝颤抖的笔迹,写着一行小字:“媛媛 & 倩倩,1995年夏。
但愿永不分离。”倩倩?我叫林媛。那倩倩是谁?
这个从未听过的名字……“永不分离……”那低语声,又一次响起了。但这一次,
它不是来自耳边,也不是来自门外。它来自……床底深处。带着泥土的腥气,
和一种仿佛积攒了二十年的、冰冷的怨恨:“姐姐……你终于……找到我了。
”那声音从床底深处渗出,带着陈年泥土的粘稠和一种刻骨的寒意,不是通过空气传播,
更像是直接在我颅骨内响起。我像被冻住一般僵在原地,眼睁睁看着床底那片阴影开始蠕动。
一只手,苍白,浮肿,指甲缝里嵌着干涸的泥垢,缓缓伸了出来,扒住了地板。
接着是另一只。然后,是一团湿漉漉、沾着草屑和泥土的黑色头发。
“倩倩……”我无意识地重复着照片背后的名字,喉咙发紧,几乎窒息。那团头发慢慢抬起,
露出一张脸。照片上的脸。档案室尸体照片的脸。我的脸。只是这张脸毫无血色,
皮肤呈现出一种被水长期浸泡后的死白和浮肿,眼眶深陷,
里面是两潭纯粹的、没有任何光亮的漆黑。她的嘴角,却挂着一丝极其扭曲、僵硬的微笑,
仿佛肌肉被强行拉扯定型。她看着我,那双黑洞般的眼睛锁定了我。
“他们说……死的那个是你……”她的声音干涩,像是生锈的金属在摩擦,
“可躺在地下……冷了二十年的人……是我啊,姐姐。”她一点点从床底爬出来,
动作僵硬而诡异,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。身上穿着的,正是照片里那件小花裙,
只是如今破烂不堪,沾满泥泞,颜色黯淡得几乎看不出原貌。手腕上,那根红绳赫然在目,
比照片里的更显陈旧,颜色暗沉如凝固的血。“为什么……”我艰难地发出声音,
握着刀的手抖得无法控制,“为什么是我……为什么你……”“为什么?”倩倩偏了偏头,
脖颈发出“咔吧”的轻响,那扭曲的笑容扩大了些,露出森白的牙齿,
“因为妈妈选择了你啊,姐姐。”她慢慢站起身,湿冷的泥水从她身上滴落,
在地板上晕开一小滩污迹。她朝着我走近一步,那股混合着坟墓和腐烂气息的冰冷扑面而来。
“那场‘意外’……”她嗤笑一声,声音里充满了怨毒,“根本不是意外。是我们太吵了?
太累赘了?还是……只需要一个‘完美’的女儿?”我后退,背脊撞上了冰冷的墙壁,
无路可退。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,砸碎着我过往认知的一切。
“她把你变成了我……”倩倩伸出那只苍白浮肿的手,指向我,又指向她自己,
“还是把我……变成了你?分不清了吧?姐姐,你也分不清了吧?
”她的目光落在我因为紧握而指节发白的手上,那根刚从卫生间捡起的红绳露出一角。
“看……”她黑洞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诡异的满足,“信物……还在呼唤我呢。”话音刚落,
我手中那根冰冷的红绳突然像活过来一样,猛地收紧!像一条毒蛇,死死勒进我的皮肉,
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和冰寒!“啊!”我痛呼出声,试图甩脱它,但它仿佛长在了我的手上,
越勒越紧,皮肤瞬间变成了紫红色。倩倩发出一种满足的、如同夜枭般的低笑。
“我们本该是一体的……姐姐。”她又逼近一步,几乎与我鼻尖相贴,
那冰冷的死亡气息几乎让我晕厥,“妈妈把我们分开了……现在,
该合而为一了……”她抬起双手,那双苍白浮肿、带着泥垢的手,朝着我的脖颈缓缓合拢。
我看着她手腕上那根暗红的绳圈,又感受到自己手上那根几乎要勒断骨头的冰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