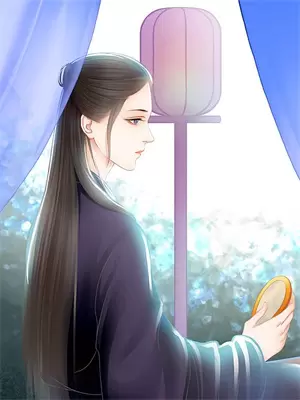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衰老混合的气味,像某种陈腐的香料。
林晚坐在病床前,看着祖母嶙峋的手死死攥着被单。老人的眼睛浑浊不堪,瞳孔深处却燃烧着一种非人的恐惧,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,仿佛能穿透它,看到某个常人无法触及的维度。
“面包屑……”祖母的声音嘶哑,如同枯叶摩擦,“路上的面包屑……被鸟儿吃掉了,不是鸟儿……是地本身,地在蠕动,在吞食……”
林晚握住祖母冰冷的手,试图给予一丝温暖。“奶奶,是我,小晚。没事了,都过去了。”
“过去了?”祖母猛地转过头,目光钉子般楔入林晚的眼睛,那力量根本不像一个弥留之人。“永远不会过去!它们在泥土里发芽,长成甜美的陷阱……糖果的墙壁在流血,糖霜是尸骨的粉末……”
这是《汉塞尔与格莱特》。林晚小时候,祖母从未给她讲过这些“美好”的童话,直到最近半年,老人精神急剧恶化,这些扭曲的故事片段才如同脓液般从她破碎的记忆中流淌出来。
“那个女孩……她推了老太婆……”祖母的声音骤然压低,充满秘而不宣的恐怖,“她不知道!她释放了……平衡被打破了!饥荒……绿色的饥荒……”
护士进来例行检查,对林晚投来一个同情而又略带无奈的眼神。祖母的“童话呓语”在整个安宁病房早已不是秘密。
夜深了,林晚靠在椅背上假寐。朦胧间,她仿佛看见一片幽暗的森林,树木的枝丫像扭曲的臂膀。地上散落的并非面包屑,而是一颗颗圆润的、如同眼珠般的石子,正被地面缓缓“吸收”,消失不见。远处,一栋用姜饼和糖果做成的小屋矗立在林间空地上,它的窗户像两颗巨大的、黏稠的太妃糖,正渗出暗色的汁液……
她一个激灵惊醒,背上沁出冷汗。病房里只剩祖母粗重的呼吸声。
“……玫瑰……”祖母又开始呓语,声音变得缥缈而诡异,“不是玫瑰,是荆棘……刺破了时间……她在里面……一直醒着……能感觉到每一次心跳,每一次被荆棘吞噬的哀嚎……”
林晚感到一阵寒意。《睡美人》。这次的呓语比以往都要清晰,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细节。
“一百年……她在永恒的‘此刻’……然后,他来了……他的吻……是虫子……是侵占……”
祖母的手突然抬起,死死抓住林晚的手腕,枯瘦的手指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她的眼睛瞪得极大,瞳孔缩成两个黑点。
“记住……晚晚……我们不是记录者……是守密人……锁链……锁链要断了……”
话音未落,那抓住林晚的手骤然松开,无力地垂落。心电监护仪上,跳动的曲线拉成一条冰冷的直线。
祖母走了。带着她那些无人能懂的恐怖童话,和她最后那句如同诅咒般的遗言。
葬礼简单而肃穆。回到祖母生前独居的老屋,林晚在弥漫着灰尘和旧时光气味的书房里,找到了那个祖母指定留给她的梨花木匣。里面没有金银首饰,只有一本以某种粗糙、厚实的皮革装订的手札,边角已被摩挲得发亮。
她翻开第一页。
手札的内页并非普通纸张,更像是某种经过处理的鞣制皮料。上面的字迹,是用一种暗褐色的、干涸的墨水书写的。那颜色,让林晚胃里一阵翻腾——它太像干涸的血迹。
开篇的文字,并非任何一种她所知的语言,扭曲古怪,仿佛活物般在纸上蠕动。但当她凝神细看时,那些字符的含义却直接涌入她的脑海:
“以血与遗忘之名,吾等立约,封存真实于故事之棺椁。”
她颤抖着往后翻。手札中夹杂着一些潦草的素描——并非用铅笔,同样是用那暗褐色的“墨”。她看到一片森林,树木的根系盘虬卧龙,紧紧缠绕着地下若隐若现的、孩童形状的轮廓。她看到一座被巨大、活物般荆棘缠绕的城堡,荆棘的尖刺上,挂着破碎的布片和疑似干瘪内脏的东西。
而在描述《汉塞尔与格莱特》的章节末尾,用更大的、几乎力透纸背的血字写着:
“代谢的均衡,以童稚之生机,换取土地之丰饶。妄动仪式者,必遭绿色反噬。”
林晚感到一阵眩晕,书房里熟悉的景象开始扭曲、旋转。她仿佛又被拉入那个梦境,但这一次更加清晰。她不仅看到了糖果屋,甚至能“闻”到那甜腻到令人作呕的、混合着腐烂肉质的香气。她“感觉”到脚下的泥土柔软而温热,如同某种巨兽的舌苔。
她猛地甩头,摆脱了那可怕的幻觉,心脏狂跳不止。
就在这时,她的目光落在手札最后一页的空白处。那里,缓缓地、如同被无形之笔书写,开始浮现出新的字迹。依旧是那暗褐色的、不祥的文字:
“下一个故事,开始了。”
几乎同时,林晚感到左手手腕内侧传来一阵灼痛。她卷起袖子,倒吸一口冷气——在那原本光洁的皮肤上,一道细小的、蜿蜒的、如同新生玫瑰荆棘的瘀青,正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刺痛感如此真实。
而窗外,夕阳正迅速沉入地平线,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,却无法驱散林晚心中那来自古老童话深处的、糖浆般粘稠的黑暗。
她知道,祖母的呓语并非疯话。
遗忘之川的守密人——她的宿命,此刻,正式降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