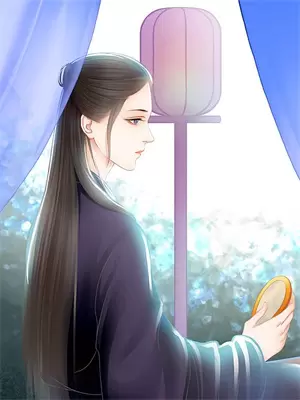1 阁楼惊魂凌晨三点十七分,阁楼的木地板又在响。不是老鼠那种细碎的窸窣,
是有人拖着脚走路,一步,又一步,像穿了湿透的棉鞋,黏在地板上,
扯起来时带着点纤维断裂的闷响。我攥着被角的手沁出冷汗。这是这个月第七次了。
去年秋天从远房表叔手里继承这栋老楼时,中介说阁楼是“附赠的惊喜”。表叔走得突然,
心脏病,倒在阁楼楼梯口,法医鉴定是深夜突发。当时我只觉得晦气,
没多想——毕竟一线城市中心区的独栋老楼,市价能让我这种刚失业的社畜少奋斗三十年。
前几次听到声响,我安慰自己是老房子的热胀冷缩。直到上周三,我半夜爬起来喝水,
撞见阁楼门缝里漏出昏黄的光。那种老式钨丝灯的光,暖得发腻,像化不开的黄油。
我屏住呼吸摸过去,光突然灭了。推开门时,只有积灰的横梁和堆到天花板的纸箱,
空气里飘着股淡淡的、类似旧书混着铁锈的味道。“谁在那儿?
”我的声音在空荡的阁楼里撞出回声,惊得墙角的蜘蛛网盘丝震了震。没有回应。
今天这声响格外清楚,甚至能听出拖动的轨迹——从楼梯口开始,
绕着阁楼中央的木桌转了半圈,停在北窗底下。然后是一声轻响,
像什么东西被放在了窗台上。我猛地坐起来,胸腔里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。
北窗正对着我的卧室,窗帘没拉严,能看到外面老槐树的枝桠在月光里晃。
抓起手机打开手电筒,光扫过楼梯扶手时,我僵住了。第三阶楼梯的扶手上,
有一道新鲜的划痕,边缘还沾着点暗红色的粉末。这扶手是红木的,表叔生前宝贝得很,
每次打扫都要上蜡。我上周才擦过,当时绝对没有这道痕。光往上移,楼梯转角的墙面上,
挂着表叔的遗像。黑白照片里,他穿着中山装,嘴角抿成一条直线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。
此刻被手机光照着,那眼神像是活了过来,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后背一凉,
手里的手机差点掉下去。2 铁盒之谜阁楼的声响停了。整栋楼静得可怕,
只有我的心跳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响。“别自己吓自己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
捡起墙角的棒球棍——这是我搬进来后唯一的防身武器。楼梯是木制的,
踩上去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,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每上一步,
那股旧书混着铁锈的味道就浓一分。到了阁楼门口,我侧耳听了听,里面没声。握紧棒球棍,
猛地推开门。手电筒的光柱在阁楼里扫过,灰尘在光里翻滚。
堆着的纸箱、落满灰的旧家具、墙角的蜘蛛网……和每次来都一样,没有任何人。
可那股味道更浓了,尤其是在北窗附近。我走过去,
窗台上果然放着东西——一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,锈迹斑斑,边角卷了毛。这盒子不是我的。
拿起盒子时,指尖触到一片冰凉,还沾了点湿滑的东西。凑近闻了闻,是铁锈味。盒子没锁,
轻轻一掰就开了。里面铺着层暗红色的绒布,放着一枚银戒指,上面刻着朵模糊的蔷薇花,
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。照片上是个穿旗袍的女人,二十多岁的样子,梳着齐耳短发,
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,手里攥着和盒子里一模一样的戒指。背景是这栋楼的院子,
老槐树比现在细得多。这女人是谁?我翻遍了表叔的遗物,从没见过这张照片。
表叔终生未娶,家里连张女性的照片都没有。正拿着照片发愣,手电筒的光突然晃了一下。
不是没电,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我猛地回头,光柱扫过阁楼门口——空的。
可刚才那瞬间,我分明感觉到有人站在那里,呼吸声就在耳边。“谁?!”我举起棒球棍,
声音都在抖。没人回答。但楼梯方向传来“咚”的一声,像是有什么重物掉在了地上。
3 白布下的秘密我顾不上铁皮盒,转身就往楼梯跑。跑到楼梯口往下看,
客厅的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,暖黄色的光铺满整个房间。而客厅中央的地板上,躺着一个人。
准确说,是一个人形的东西,被一块白布盖着,轮廓和人一模一样。我的腿像灌了铅,
怎么也迈不动。那白布边缘渗出血迹,暗红色的,正慢慢往四周晕开。
和楼梯扶手上的粉末颜色一样。“表叔?”我试探着喊了一声,声音在喉咙里打了个转。
没人应。阁楼的门在我身后“吱呀”一声,像是被风吹得关上了。我猛地回头,门确实关了。
可我明明记得刚才没关。再转回来时,客厅里的白布动了一下。不是风吹的,
是下面的东西在动,像是有什么在里面挣扎,白布被撑起一个不规则的弧度,然后又塌下去。
血渗得更快了,在地板上积成一小滩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剩下一个念头:跑。
转身想往楼下冲,脚刚踏上楼梯,就听到身后传来布料摩擦的声音。回头一看,
那白布被掀开了一角,露出底下的东西——是一件中山装,和表叔遗像上穿的那件一模一样,
胸前染着大片的暗红,像是干涸的血迹。而中山装的领口处,搭着一只手,皮肤皱巴巴的,
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那只手动了动,像是要抓住什么。我尖叫一声,转身就往楼下跑,
棒球棍都扔了。楼梯太陡,我摔了一跤,膝盖磕在台阶上,疼得钻心。但我顾不上,
连滚带爬地冲到一楼门口,摸到门把手时,发现门锁是锁着的。我明明记得睡前没锁门。
钥匙串就在门边的鞋柜上,可我手抖得厉害,怎么也插不进锁孔。
身后的楼梯传来缓慢的脚步声,一步,又一步,和阁楼里的声音一模一样,拖着脚,
黏在地板上。“别过来……”我哭出声,钥匙终于插进锁孔,拧了半圈,门开了。
我连滚带爬地冲出去,摔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。深秋的夜里,露水打在身上,冷得刺骨。
回头看时,二楼的窗户亮着灯,窗帘上印着一个模糊的人影,正对着我,一动不动。
我爬起来就往巷口跑,直到看到街灯和偶尔驶过的汽车,才敢停下来喘气。手机还在口袋里,
我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。4 年前的真相警察来的时候,我还坐在马路牙子上,浑身发抖。
他们跟着我回了老楼,院子里静悄悄的,楼里一片漆黑。“你确定看到人影了?
”带头的警察皱着眉问,他叫李建国,四十多岁,眼神很锐利。“确定,还有阁楼的声音,
客厅的白布……”我语无伦次地解释。李建国没多说,带着两个年轻警察进了楼。
我不敢进去,站在院子里等,心脏还在狂跳。十几分钟后,他们出来了。“屋里没人。
”李建国的表情很严肃,“阁楼我们也查了,除了些旧东西,什么都没有。客厅地板很干净,
没有血迹,也没有白布。”“不可能!”我急了,“阁楼里有个铁皮盒,还有张女人的照片,
你们没看到吗?”“没有。”李建国摇摇头,“阁楼里是有不少箱子,
但我们没找到你说的铁皮盒。倒是在楼梯扶手上发现了点东西。”他拿出一个证物袋,
里面装着一点暗红色的粉末,“回去化验一下,看看是什么。”我愣在原地,说不出话。
他们又问了些细节,做了笔录,让我先去朋友家或者酒店住,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。临走时,
李建国看着我说:“这栋楼以前出过事。”“什么事?”“三十年前,表叔的妹妹,
就是你表姑,在阁楼里自杀了。”李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也是心脏病发,和你表叔一样。
”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表叔有妹妹?我从没听说过。“她为什么自杀?”“不清楚,
当时案子结得很快,说是突发疾病。”李建国顿了顿,“不过街坊邻居有传言,
说她是为情所困,那男的最后没娶她,还骗走了她不少钱。”我想起那张照片上的女人,
穿旗袍,戴蔷薇戒指,笑得那么甜。是她吗?警察走后,我不敢再进楼,
揣着手机在巷口坐了一夜。天快亮时,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是陌生号码,
只有一张照片——还是那个穿旗袍的女人,站在阁楼的北窗下,手里拿着那个铁皮盒,
背景里能看到我卧室的窗户。照片上的时间显示,是十分钟前。我猛地抬头看向老楼,
二楼的窗户黑洞洞的,像一只盯着我的眼睛。第二天,我去了档案馆。查了三十年前的报纸,
果然找到了一条短讯,说XX街老楼发生意外,
住户林秀雅也就是我表姑深夜心脏病发去世,年仅二十五岁。报道里没提自杀,
也没提男人。但我在当年的户籍档案里找到了林秀雅的照片,和铁皮盒里的女人一模一样。
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,档案里写着,她的死因是“急性心脏衰竭”,死亡地点是“阁楼”,
发现人是“其兄林正德”——也就是我表叔。表叔发现了她的尸体。我拿着档案去找李建国,
他看了很久,说:“我查了一下,当年的卷宗里有个疑点,林秀雅的指甲缝里有皮屑,
不是她自己的,但当时技术有限,没查出来源。”“会不会是表叔的?”我问。
李建国没回答,只是把那份暗红色粉末的化验报告递给我。上面写着:成分是氧化铁,
也就是铁锈,混合了少量人类血液,血型为A型。而表叔的血型,档案里记着是A型。
5 复仇的幽灵那天下午,我又回了老楼。不是不怕,是心里有个声音在催我,必须弄清楚。
阁楼的门虚掩着,那股旧书混着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走进去,北窗下的地板上,
放着那个铁皮盒,和我昨晚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打开盒子,戒指还在,照片却换了。新照片上,